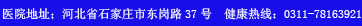同衡学术丨社区治理重构背景下的规划公众参
2022/10/8 来源:不详导
读
近年来,随着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等社区组织的兴起,居委会的权力开始受到挑战,各类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正在扮演越发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南京小卫街社区营造为例,通过归纳分析社区治理主体、社区治理格局演变等方面,提出多元共治框架和公众参与平台,是在社区治理重构背景下的一种全新尝试。展望未来,在涉及改造尺度较大的规划项目中,可以小卫街社区营造模式为范本,构建起以两类非政府组织为核心的规划公众参与机制,推动存量时代和治理重构大背景下规划范式的全面变革。
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宣讲论文作者:杨钦宇单位: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中心三所
01
社区治理格局的变迁
自“单位制”解体以来,中国基层治理的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单位人”重新成为“社会人”、“社区人”;另一方面,改革造成的治理真空被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充,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种政府实体,城市治理并未向自组织的趋势转变。作为社区自治法理上的承载主体——社区居委会,长期以来一直扮演着政府行政末梢的角色,成为行政事务管理的辅助性机构,居民的自治权不被重视,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多为动员式参与、自愿度低。
近年来,随着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等社区组织的兴起,居委会的权力开始受到挑战,各类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正在扮演越发重要的作用。如清华大学“新清河实验”课题组和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作为第三方智力支持机构,分别在北京市清河街道、大栅栏街道开展社区营造活动,而厦门、成都、佛山顺德区、上海嘉定区、南京玄武区等各地均出台了大量关于推进城乡社区营造的系列政策,各地专业性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社会组织凭借专业技能参与社区治理,使中国的社区治理从依靠“居委会大妈”的个体经验治理向借助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治理转变。
清华大学“新清河实验”
由此,在社区治理格局发生重构的背景下,社区治理应是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社区利益组织(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兴趣类组织等)、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公共/专业服务提供者)、社区居民以及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基于公共利益和社区认同进行的协商、互动和合作,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
02
规划公众参与的新趋势
由于政府和规划师均非维护公共利益的“道德超人”,因此基于公益和志愿性质形成的非政府组织,能在更大程度上抛开私利,在规划公众参与过程中担任协调各方利益的组织协调者具有天然优势。而在广州恩宁路街区、厦门兴旺社区和西山社区、都江堰灾后重建社区、成都北部片区改造等大量规划实践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利益团体正在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协作共治的规划模式。
各规划实践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和利益团体
一般来说,尺度越小的规划项目,与产权所有者的关系越紧密,公众的自组织性越高,参与的深度越大,公众意见在决策中所起的分量也越重。而社区作为基层自治单位,社区规划与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居民参与社区规划的意愿也会更高。在中国市民社会逐步发育的过程中,以社区/街道为单元,以公众参与为导向的社区微更新、社区/街道规划为试点,是探索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新模式的突破口。
伴随社区治理格局的变迁,以第三方社会组织为核心,作为社区规划的组织协调者,搭建政府、居民、规划师、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等多主体协调沟通的公共参与平台,正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社区规划公众参与的新趋势。
03
案例:南京小卫街社区营造的探索
南京小卫街社区营造正是非政府组织介入社区规划的典型案例,由区政府委托的江苏华益社会组织评估中心(以下简称华益)承担公众参与的组织者,由其培育建立小卫街社区治理发展协会则作为社区的自治组织,组织者通过撬动政府、社会、高校等资源,有效推动社区更新的规划和实施,并利用社区营造的契机为社区治理转型注入新的动力。
01
背景与概况
小卫街社区建于年代末,由铁匠营(农民安置小区)、都市山庄(中高档商品房小区)和七二四所家属楼构成。坐落于明孝陵下马坊东侧,与中山陵、明孝陵等景区及下马坊公园毗邻。同时背靠环紫金山绿道,拥有绝佳的休闲运动场所。辖区及周边有南理工、金陵专科学院、南农大、南京体育学院等大专院校。
小卫街社区平面图
社区周边的休闲运动资源
02
社区问题诊断
社区主要存在人与空间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居民构成中大多是失地农民、老人,收入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医疗开支占比很大,健康成为社区居民的重点